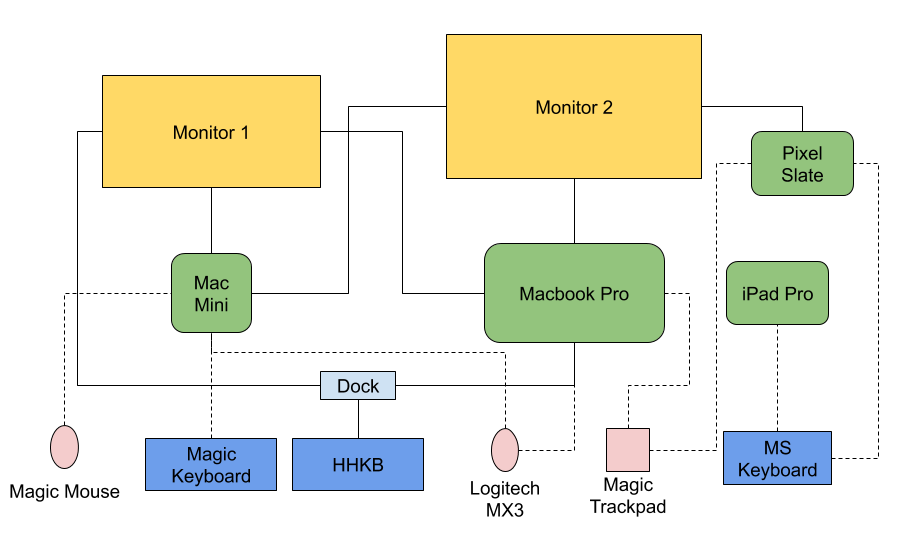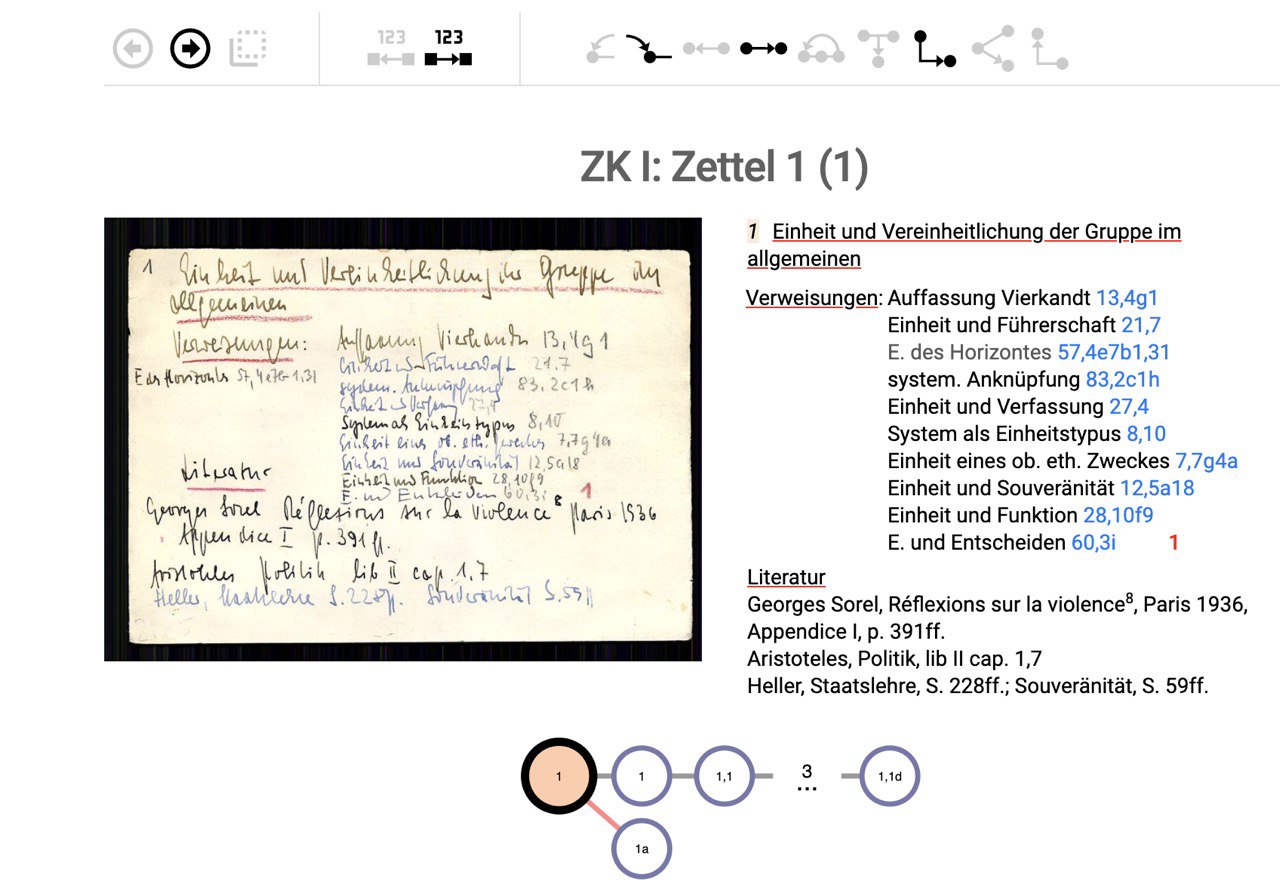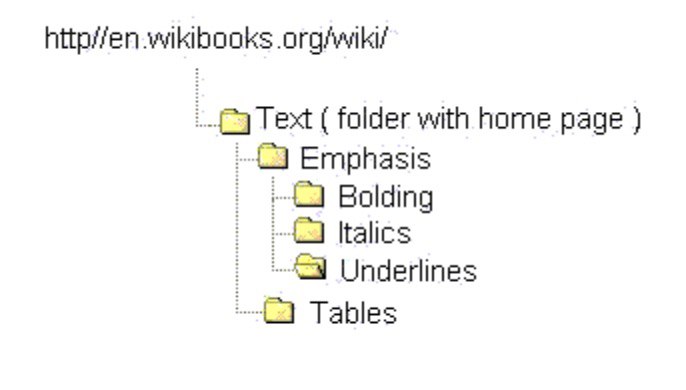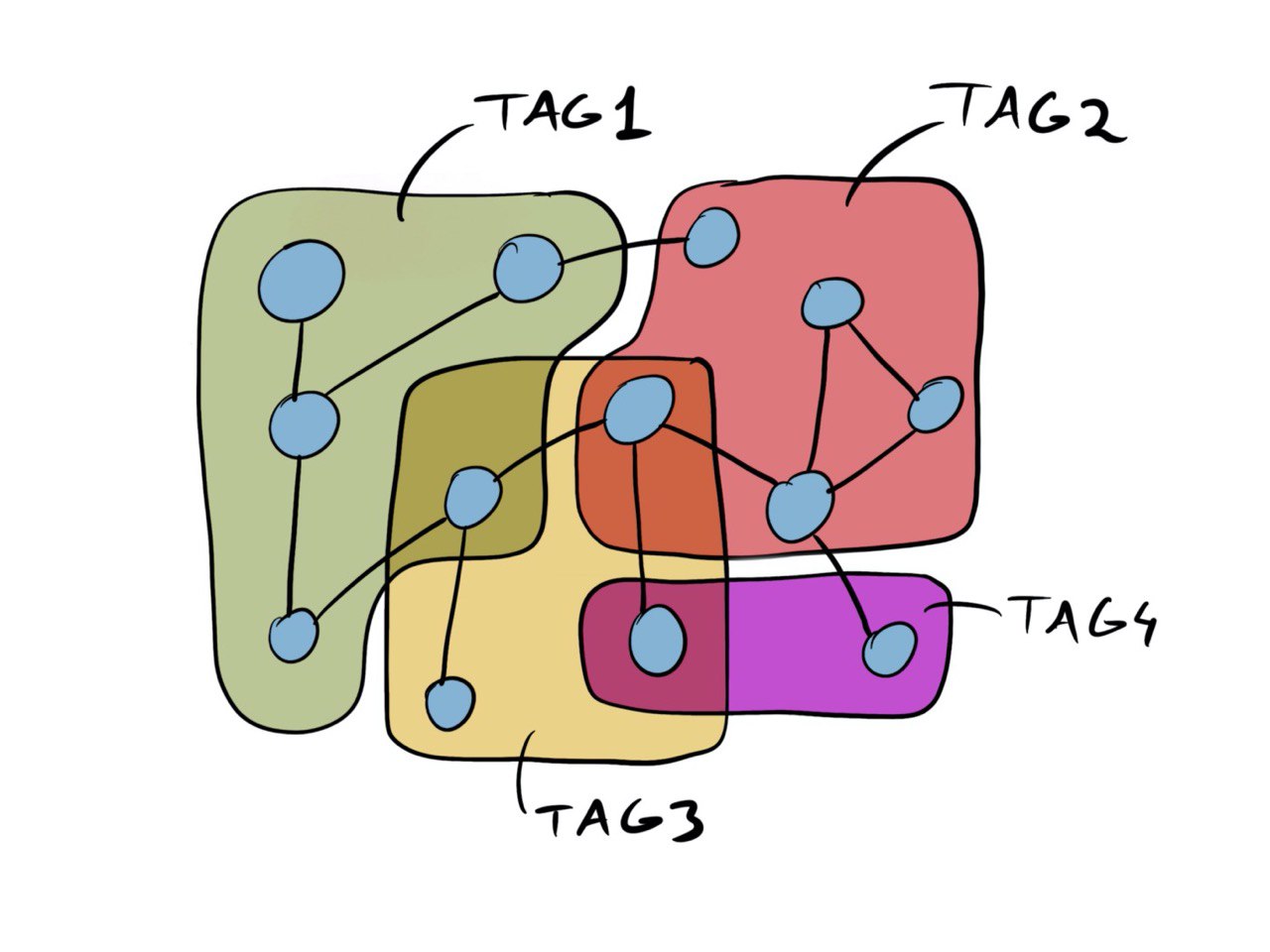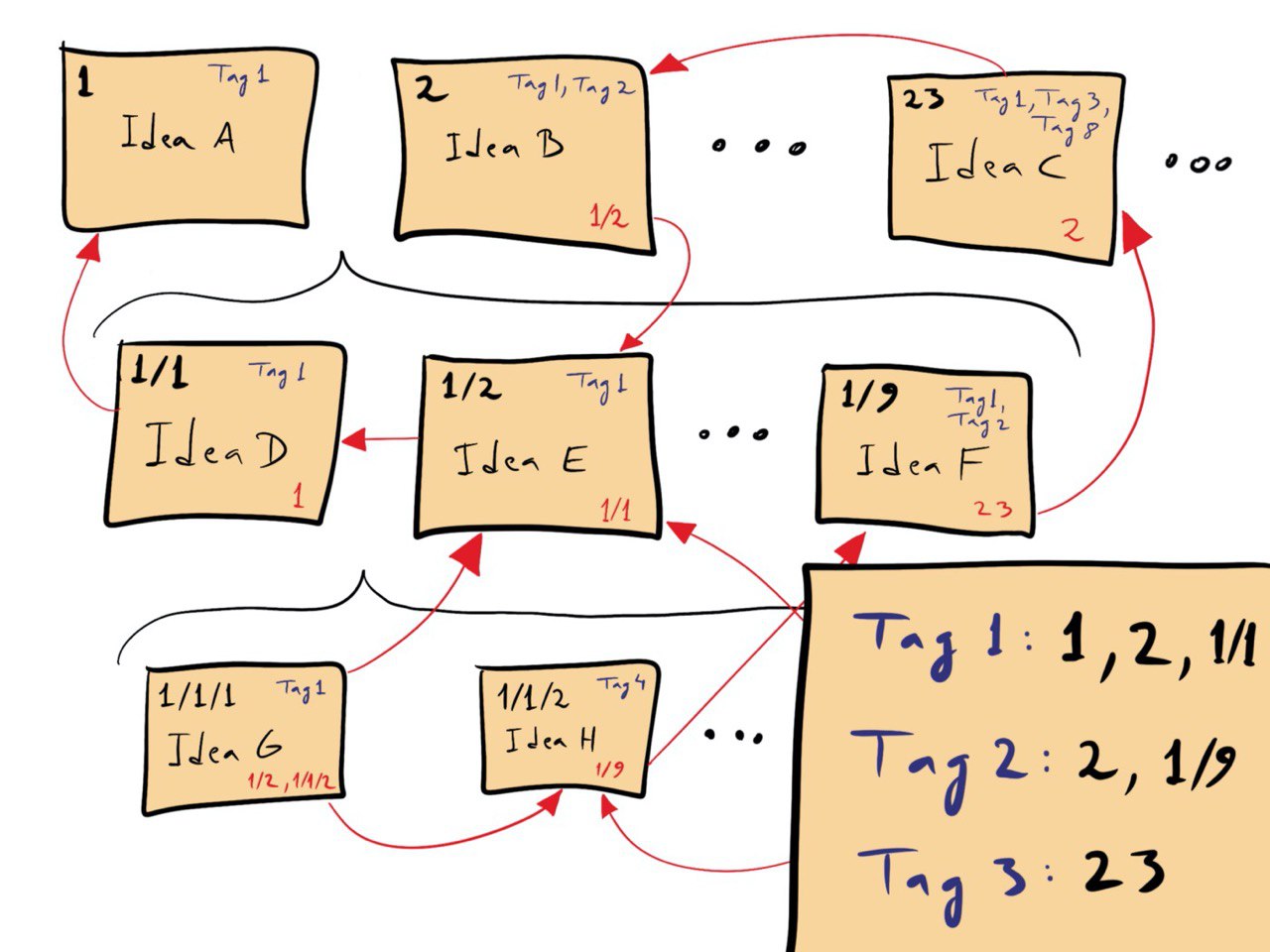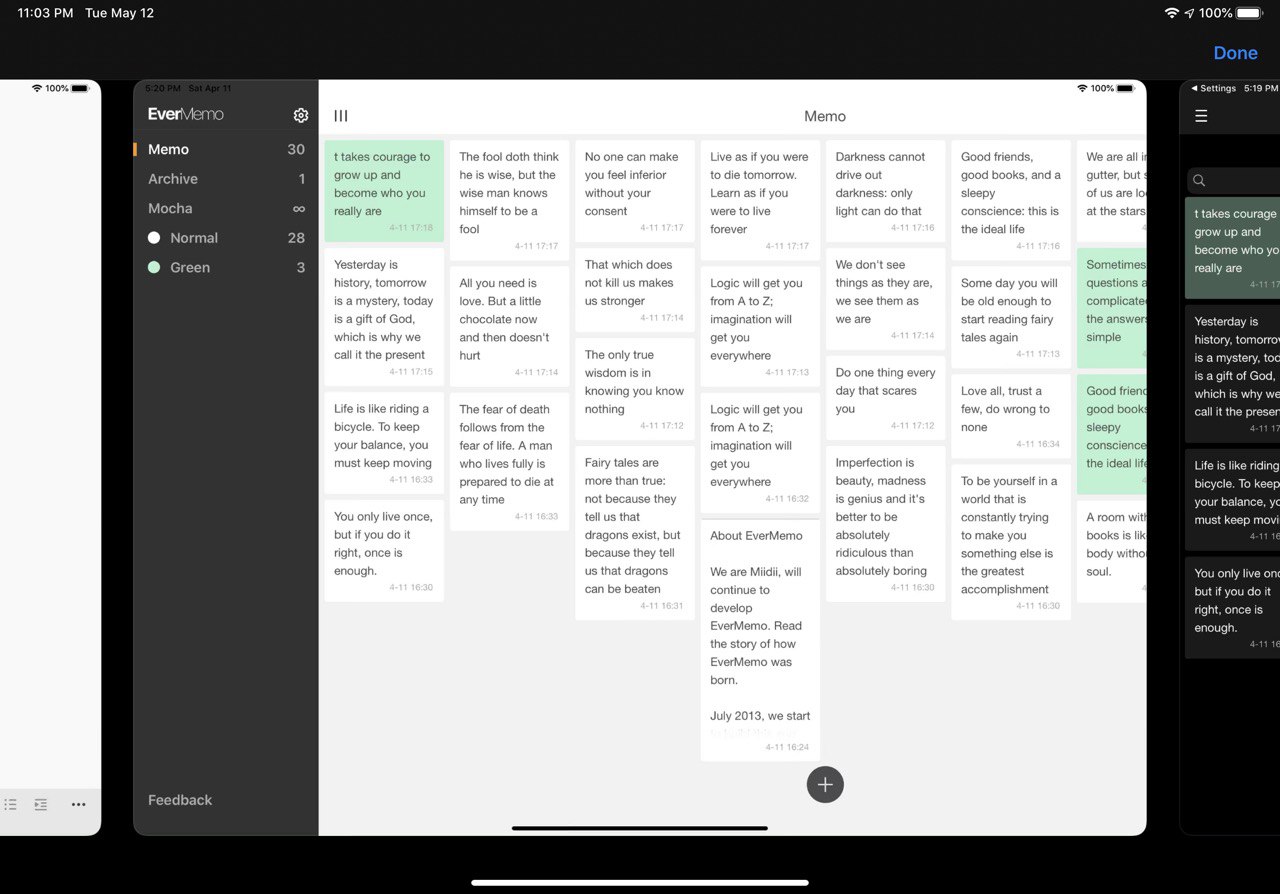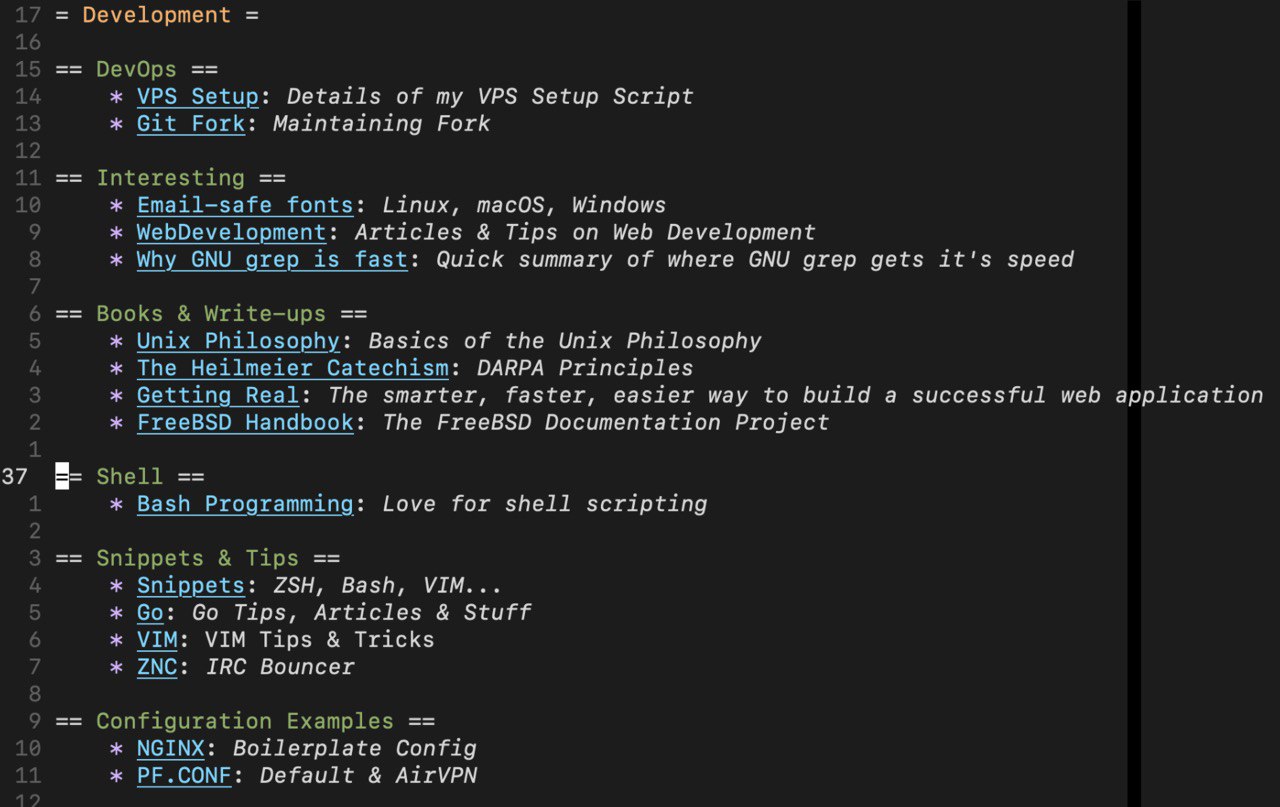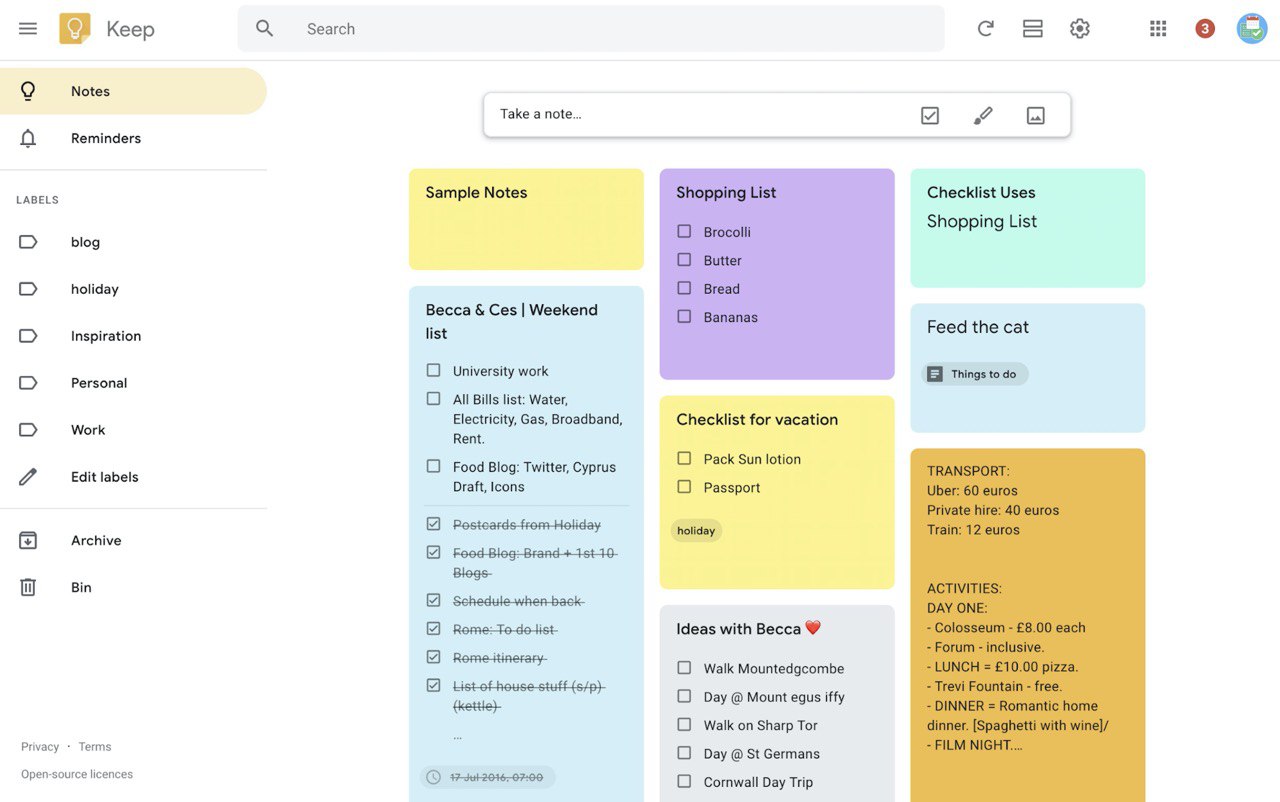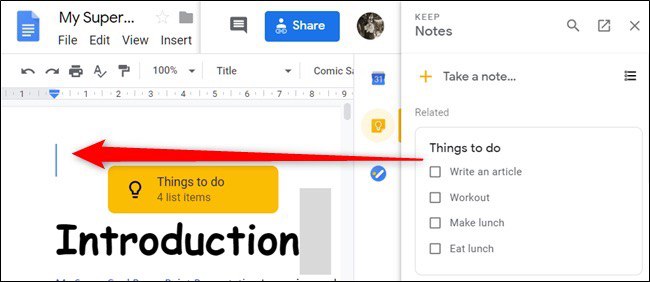首先不要把这本书看作是学术著作,具有老华人老学者传统爱国热情的通俗历史科普读物。唐德刚主要做口述史,胜在作者和时代中人的关系,顾维钧、胡适、李宗仁他都有接触,能从比较细节的方面回看历史。但我觉得他对民国和孙中山有一层滤镜,当然这来自于他一腔爱国之心。
袁氏当国是他清末掌权到称帝的时期,一个封建老官僚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做上总统,又如何被黄袍加身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时也势也。但假如民国初年就能把国体问题解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并且各方平衡的态势下循序渐进,那我只能说中国太过幸运,不过没有哪个国家能那么幸运,总要有波折有反动有折腾。
唐德刚就有历史三峡观:「他將四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變遷分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階段。其中要經歷兩大歷史三峽,也就是要經歷兩大歷史階段的轉變。“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 。「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 。並說經歷約200年,到大約西元2040年,中國歷史將會走完第二個「長江三峽」,迎來「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新時代。」
但他没有讲清楚我们要坐什么船过这个三峡,新时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
回到这本书,体例上是时间顺序,但是主题比较松散,某个小节可能突然介绍某人生平,某个小节突然介绍文化,或者时代背景。当然这些都是相关的内容,只是容易跳跃。我粗读这本书,主要是大概了解民国建国初年的历史及袁世凯称帝始末。所以我主要看三条线,第一,民国初年登场的各派势力及他们的利益,第二,国体之争,如果变为共和,共和又如何变回帝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的矛盾,第三,外国势力如何干涉我国内政,影响当时的政治格局。
利益团体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民国之初,万事未定,各路人马蜂拥而出,各个占山为王,大党小党,而且这些党不大有什么纲领与章程,都是一些小的利益集团。
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把登台的大小人物定位准确,知道他们属于什么班子,班子之间的权势起伏,对了解整个历史形势很有帮助。看上去民国初年,虽然大家各有山头,但是总体还是为了国家,袁孙之间能有共识。袁在这方面可以说很大度,他做总统没有折腾,更像是个定海神针的位置,稳住各方势力。当然也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旧官僚对共和这一套不了解不熟悉,一切都还在摸索和观察中,这也很符合他的性格和行事。他来做第一个大总统不可以说不合适。
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世凯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
然后刺宋案的结果导致了袁孙的分道扬镳,这是历史的偶然。假如此时没有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北洋政府时期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让新的共和国休养生息。
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文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学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
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幅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我们对孙中山有国父光环,但其实他当临时大总统就有「下山偷桃」之嫌,而且只会说大话,实事做得少,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革命性。但宋案后孙不够理智,也不走法律框架,一上来就二次革命,但又没有足够政治和军事资本,最后兵败流亡。从此平衡就打破了,袁不再束手。终究是成王败寇的那套逻辑。
当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等人,都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除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且孙逃亡日本时改组国民党时提出要独于一尊,就连同盟会老人们都未必同意,但是他坚信这是中国的必经之路,军政、训政,宪政。蒋介石继承他的衣钵做独裁也很自然。
想说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近代史的历史叙述里面,要么是共产党的史观,那么就是用阶级来分类,主要的矛盾是共产党和反动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而是民国的史观,更多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视角,这里面也是把国民党视为天生的主角,北洋的历史往往是负面的,因为毕竟「北伐」是其功绩。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有很多面向,继承了晚清的各路班子,有新有旧,有左有右,是很丰富的时期,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
同盟会一派
黄兴,参加武昌起义,第一号战将。做过一段时间南京留守,处理烂摊子。主和派。
宋教仁,光芒四射、才气逼人,但过于招摇: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
宋一上来就想做党派政治,一党专政。
胡汉民,粤督
这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两千余年未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余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踞本省的恶例。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想反袁,却都不敢反袁。
汪精卫,声名甚高,同盟会中亲袁。袁让他和袁克定做拜把兄弟。
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之上。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
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尚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
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二次革命也有和战之分。
国民党内部从头到尾就是不断斗争。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后来改组国民党想要做寡头。
共进会
因有武昌起义之功,所以有政治资本。
黎元洪,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
黎元洪后来出卖了三武,投向了袁世凯。后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北洋
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北洋军,段祺瑞,冯国璋
蔡元培曾领队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做总统。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
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婉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陆徴祥,赵秉钧,内阁大臣。
唐绍仪,孙中山的同乡,美国留学,在朝鲜与袁世凯相熟,一路跟着袁世凯过来的。后加入同盟会。袁内阁的总理,本来是个合适的人选。但是袁世凯已经想要独揽大权,内阁再好,总理再合适,也只是摆设了。
老君主立宪派,保皇派,进步党
张謇
熊希龄
因此纵是同盟会中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孙、黄、汪、胡、蔡、吴等人,对他们也英雄识英雄,颇具敬意与好感。袁世凯在赶走国民党之后,起用这批新人,纵是国民党人也承认熊氏的内阁是第一流内阁。
想改革,也只能失败。
梁启超,蔡锷
师生关系
袁世凯后来想用蔡锷再造新军,梁启超也支持。袁世凯称帝之后这两人一文一武首先反袁。
唐继尧是蔡锷提拔的,后来云南起义并没有完全支持蔡锷。
以上是几个主流的势力,可以说彼此有融合,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假如能够放下私利,为一个更高的目的而团结起来,这班精英是有能力再造新中国的。但是满清倒的太快,这群人对共和的理解只是皮毛,当然只能互相倾轧先来追求私利了。
国体之争
总统制与内阁制
同盟会一帮人是完全以美国为蓝本来建国的。然而又不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为了限制他的权力,就只好在约法里做手脚,用内阁制的总理来限制总统制。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
特殊的形势导致了国体的矛盾,总统和总理之间必然是要争权的,引起了后面的反复,甚至是「府院之争」。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笔者在前一章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他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
孙袁两方都有妥协,但都想绕过对方。民国的建立主要靠两股势力,一个是同盟会代表的南方革命派,粤鄂江浙势力为主,一个是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旧官僚对上了革命者,很难形成共识。但我觉得一开始两方都较为克制,很难得。想要超越这种矛盾,为了大刀阔斧地干,只能清除另外一方,做成独裁。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
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但这些都是精英视野,在那个时候,能了解西方那套体系的是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人。若要问民意,百姓还是相信明君。你跟普通人讲总统是皇帝,总理是丞相,他就懂了。这需要几代人的教育才能扭转,不能跳出时代背景。
按参议院制定的、由袁大总统于1912年8月27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学会(中央学会是一个由教育总长领导的,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专家学者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迄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八十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呼之为“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6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680—747页)。
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女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有影响的人,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什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她们闹了一阵,未闹出什么结果来,也就算了。
一开始还是有模有样在组织参议院和众议员。政体之争的转折点在于宋教仁被刺杀。
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百九十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不一定要杀宋,要笼络他,汪精卫也是亲袁。作者觉得是总理赵秉钧利用早期的特务做掉了宋教仁,为了讨好袁世凯,未必是袁世凯的本意。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也以全盘失败告终。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
本来共和这个国体已经得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
作者的评价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也是一转百转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作客观实在。
但是老百姓没有有体会到共和的好处,说不定还觉得有皇帝的日子舒服些。也是民国来得太容易,上车的都是些投机分子。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什么,愤些什么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都想过上美国式的好日子。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在上篇拙作里,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账不能都算在袁氏一个人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national consensus):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章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道)。
作者还认为帝制的独裁和新式的独裁不同,新式独裁继承下去权力总是能递减的。比如蒋介石传给蒋经国。但是蒋经国总是特例,看看金家就知道了。即使不说自己是皇帝,也可以做得到同皇帝一样的独裁。
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后:
一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他们认为没有宪法,哪来总统呢?另一派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他们的理由是,制宪乃百年大计也,不妨慢慢来,而选举总统则是当务之急。因为民国成立一年了,列强至今还在观望,没有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权。我们连个总统都没有,何能要求列强承认呢?两派原来各有各的理。二次革命后,袁氏权力陡增,他就坚持先选举,后制宪了。果然在他当选之后,英、法、俄、德、意诸列强都纷纷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了。
他们试图制订出一部详尽的宪法草案来,这便是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所谓《天坛宪法》是也。可是此时的袁世凯,不管是天坛、地坛,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天坛宪法》(全名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经国会于1913年10月三读通过,但最终还是成了一张废纸。
临时约法到,天坛宪法。最终袁世凯并没有用天坛宪法,而是对老约法修修改改,让它更符合自己的利益。然后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前期模仿美国的尝试到此结束。
大位既正之后,袁氏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国民党,彻底镇压乱党暴徒。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凯的确杀了不少国民党党员。长话短说,袁氏正位之后,首先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党员,一时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杀国民党最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党所拥护而成为开国元勋的“忠厚长者”、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
时未逾月,袁再度于1914年1月10日发布解散国会文告数千言,这个美国模式的中华民国国会,也就寿终正寝。
熊希龄内阁,此时已经没有实权,完全变成袁世凯的傀儡了。
第一,为防制藩镇,他要裁军废督;第二,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贯彻中央政令,他要虚省设道,实行省、道、县地方三级制。总之,熊氏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1913年11月15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袁世凯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想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来说更急迫的事务。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
政府乃据此于1914年1月26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3月18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5月1日公布了。
再到中华民国约法,
- 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曰立法院
- 在立法院未成立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
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
可以传妻传子的总统法。
袁逐渐做政治改革,从共和回到帝制的过度。
- 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恢复了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
- 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 各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官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
真要做成了,倒是没有后来的军阀混战了。
共和与帝制
袁不是非当这皇帝不可,袁世凯自己想当,一开始有顾虑。但是看到民意汹汹,就像顺水推舟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虽然做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诱惑力很大,他也永远热衷,但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始终犹豫不决。而杨度等不知袁氏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着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式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世凯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其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也。
可以说他也是被加速主义给害了,他甚至踩过刹车,但是无奈车子已经失控,最后总会翻车。
美国顾问古诺得教授不知中国特色,主动递了刀子。
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这时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含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共和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共和,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
杨度奇人,但是为害不浅。
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1915年6月22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虽然做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诱惑力很大,他也永远热衷,但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始终犹豫不决。而杨度等不知袁氏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着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式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世凯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其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也。
袁世凯在意日本的看法,袁克定造假的《顺天时报》让他误以为日本是支持他称帝的。但我觉得这个因素可能被夸大了,袁要了解信息一定还有别的渠道。
《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要求”谈判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袁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
反对派
二儿子袁克文名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导致舆论爆发。想要当皇帝还不知道封口,要么说袁世凯太幼稚,要么说当时的舆论太过自由。
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云南起义。各地响应。
袁世凯旧部也不服,段祺瑞,冯国璋,本来他们指望着接着当大总统,帝制之后只能服侍「曹丕」了,结局可能更惨。
于是帝制匆匆结束,开启北洋军阀时代。
境外势力
外交总长是首席。因为当时处理外交关系最为重要。
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
中国过于庞大,一下子吞不干净,反而让他们彼此制衡,不敢轻举妄动。
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西藏:
英国与俄罗斯彼此制衡。利用宗教领袖是传统艺能。英国在各地做地缘政治的搅屎棍也是老戏码。遗留了藏南问题。
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双方已正式与非正式签订过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1893)、《拉萨条约》(1904年,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修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
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俄人不遑南顾之时,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国际形势,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荣赫鹏(Sir FrancisYounghusband)指挥之下,于是年夏季一举将拉萨占领。
英人企图重据西藏的第一步,便是在班禅、达赖这两位出家人身上打主意。在班禅主政期间,英人曾乘英王子访印之机,力邀班禅赴印观礼,另作企图。然当时班禅在藏究不若达赖之有潜力也,一有机缘,英国人为其永恒的利益,就迅速舍班禅而就达赖了。原来达赖在库伦一筹莫展之时,乃回向清廷,请求入觐。此时慈禧与光绪虽已在死亡边缘,仍许其朝觐,而优礼有加,并允其回拉萨,复主藏政。
达赖回藏后,对主政缺乏自信,乃为英人挟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国,而尽褫其封号。
英人无端割裂我国如此大块疆土,我方当然坚决反对,北方大熊之俄国,此时对英国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视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顾虑。斯时适值欧战爆发,英国对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会议也就无果而终。然其后遗症,则至今犹存也。
据《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图籍所统计,达赖所辖寺庙凡三千五百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两千五百有奇;黑头藏民(俗民、农奴)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每户平均五口?)。班禅所辖则三百二十七庙,喇嘛一万三千七百有奇;黑头藏民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见同上《清史》,第5728页)。其他边区居民则为无数说汉藏语系(Sino-Tibetanlanguages)汉化或半汉化(Sinicizedor Semi-Sinicized)的生熟番民,台湾所谓原住民也,由领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统治之
蒙古
沙俄和日本瓜分。
到辛亥革命前后,俄、日这两位邻家,又进一步把中国的内蒙古一分为二,划为东西两部分。东内蒙古属日本,西内蒙古属俄国。
俄国既有此侵略满、蒙的企图,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国内乱之时,俄人即认为搞外蒙独立,此其时矣,乃唆使库伦(今乌兰巴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蒙古国,向清政府宣布独立
一战时期,各国自顾不暇,或者彼此有内部交易,都对沙俄的动作三缄其口。
俄国促成外蒙独立而不直接占领,是建一傀儡争权置其于统治之下。免得别的国家效仿,影响其在别的地方的利益。
蒙古人并不是都想分独立。蒙古贵族在清朝和满族同等地位,享尽优待,而且在北京养尊处优久了,对大清有认同感,毕竟自己的元也是占领过中国的,独立出来最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
再者,俄国人那时在库伦也专以活佛为对象暗动手脚。他们要扶植这些亲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当总统,这就不是习惯了满蒙一体、在北京过惯了贵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还有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理所应当。拿俄国人的钱,看俄国人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
和汉人打交道还有便宜占。
中西有别。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而西方帝国主义则是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
十月革命一起,蒙古主动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回归。但是收复蒙古的将领行事过于血腥,斩断了民众对中央的好感,这种外力反而推得越来越远。处理一些地方问题时需要警惕,不要重蹈覆辙。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徐树铮),错在小徐。”
东北(满洲)
俄国人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一直把我东北视为禁脔,志在全吞而后已
日俄战争之后,两方密谋瓜分东北,北满为俄所有,南满为日方所有。
山东:
一战之后,欧洲国家自顾不暇,日本找到机会想要称霸东方。提出「二十一条」
作者非常讨厌日本,他还参加过反日游行。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欧美帝国主义。它乘一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
日本迫不及待,8月23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径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英日同盟,日本急着想趁一战拿到德国占领的胶州半岛。德国却有意直接归还中国。
「唐德刚不但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作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积极参与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海外发起保卫钓鱼台行动,他是最早参与者之一。他还是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偿的呼吁者,2002年时与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一道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行动,抗议日本右翼登钓鱼台,并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款。他反对台独,曾与台独人士辩论时,被打致牙崩血流。」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要求”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文撰写结论时,于1998年9月21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
二十一条
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词。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进行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客观条件来说,北洋政府战或不战,都敌不过日本,恐怕二十一条必须得签。只能外交上拖延。外交上已经做了最好选择。最后的版本去掉了一些很不利的部分,特别是第五条。
可以看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但是历史课本对袁签二十一条的评价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当皇帝。这是不够准确的,日本眼里袁世凯是亲欧美派,欲除之而后快。袁当了皇帝是损害日本利益的。所以日本乐于见到袁世凯失败。
总结
袁世凯之当国正值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枘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枘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时代进程中悲剧人物,我认为总得来说袁世凯算是一个温和的独裁者,内忧外患之下也有稳定大局的功劳,没有称帝的闹剧,或者闹剧后能够多活几年好好收场的话,结果可能没有那么糟糕。
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于此。袁氏自知不起,在6月6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深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袁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断根,撤销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