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待久了,我对四季的敏感度也降低了许多,但是每当秋天来了,我总是想去一个有秋天的地方寻找一些证明。那些证明,是从小熟悉的植物,它们是视觉的回忆,比如红色的枫叶黄色的银杏,同时也有嗅觉的如桂花,味觉的如枇杷。但是在美国找到它们并不容易,因为它们生长在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区域,适应某一种特定的气候,「树挪死,人挪活」,四处漂泊的我在某些时刻会羡慕这些哪也去不了的植物。
不过美国的移民历史够久,有各种各样的人把它们家乡的风物一并带来了,其中就有这些「故园花木」。
桂花
首先是桂花,桂花的好处是味道先声夺人,你不需要看见它才知道它的存在。我在美国就有几次和桂花这样不期而遇,在不抱任何期待的情况下突然闻到一股桂花香,是人生最美好的瞬间。
一次是在布鲁克林植物园,在一栋温室建筑里,周遭都是一些热带植物,但一阵淡淡的桂花香就在湿度极高的温室里突然飘进了鼻腔。起初我是犹豫的,因为湿度并不是我记忆中的秋天的湿度,所以味道似乎也不完全让人确信。看了一圈,没有看到桂花痕迹。但鼻子还是没有放弃,我就跟着嗅觉继续走,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没有人的地方,看了长着一簇簇小小桂花的桂花树。我激动地在这棵树边上待了很久,闻了又闻,捡起地上散落的一些桂花,包在一张纸里面,我还仔细看了树的名牌,「亚洲树木」云云。走的时候我还对朋友说将来如果来纽约,我知道秋天该来哪里。
另外一次是在旧金山,因为住在旧金山有一段时间了,也四处查过,没有找到,所以没有什么期待。但因为朋友都知道我喜欢桂花,我的生日也正好是桂花季前后,往年我收到过桂花蜜、桂花干、桂花蜡烛等各类桂花礼物。有一天就有人发信息告诉我似乎在某地闻到了桂花味,但因为要赶车所以没有能细找,但把这个情报告诉了我,像是间谍之间接力一样,她相信我一定能找到。我一查地址,其实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而且就在上班的楼下。我立马跑过去——准确说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更快。骑到某个地方的确闻到淡淡的桂花香味,但我怎么都找不着,仍然靠着嗅觉,在一排景观树木高处找到了非常少的桂花簇。我的印象里,桂花的树冠是圆形的,大的桂花树长得很圆很宽,就像一颗巨大的花椰菜,我还记得南京灵谷寺的金陵桂花王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但这里的桂花被挤在一排花盆里,在地下车库入口处像是卫兵一样高耸地站着,它们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开的花也极少,但是味道却没有变。于是我在家的附近也有一处可以信任的秋天的据点了。
除了这两处不期而遇,还有一处是我专门挑选秋天去拜访的。波特兰的兰苏园。我在春天就去过兰苏园,在波特兰破败的中国城里面。门口的白人老奶奶激动地向我讲解汉人和满人的区别,表示清朝是蛮夷入主文明世界。她特意给我展示朱元璋的画像和满人的画像以示服饰发型之区别,我万万没想到第一次的「悼明」体验来自波特兰。因为波特兰和苏州是姐妹城市,园子是苏州派人来造的,「兰苏园」也因此得名,建筑和布景的味道都很正。美中不足是远处高楼破坏了景致,时时提醒你这在美国。秋天再去则是为了桂花。桂花在园中一角,但香气弥漫在园子里。当你找到一棵之后会发现旁边还有一棵更大的。大大小小大概有六七株。而且有金桂花,也有红橙的,也有偏白的。我怀疑造园的时候特意要把桂花当成重点,毕竟是苏州的造园工匠,懂得苏州人想要的。

枇杷
枇杷在湾区不算少见,有院子的人家会种上一棵等待季节吃枇杷。我对枇杷的记忆主要是味觉的,不由得想起最好吃的「东山白玉枇杷」。今年在旧金山的 farmer market,我甚至买到了现成的枇杷。

后来我还发现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地图记录所有已知的枇杷树:枇杷分布地图。 但我没有特意寻找过。直到有一次去 LA 的 Huntington museum,在里面的苏州园林正好碰到满开的枇杷。枇杷在苏式庭院里就特别合适,特别是要和芭蕉种在一起,一片绿色之上有点点黄色圆球,仿佛珠玉。

玉兰
小时候住的小区有很多玉兰,春天的时候开满了,白得耀眼。我在美国没有特别注意过玉兰是否常见,但旧金山植物园春天会办玉兰展。
Admire the sights and scents on the branches of more than 200 elegant trees, as velvety silver buds and saucer-sized pink, white, and magenta flowers make an appearance in this always spectacular annual bloom at the Gar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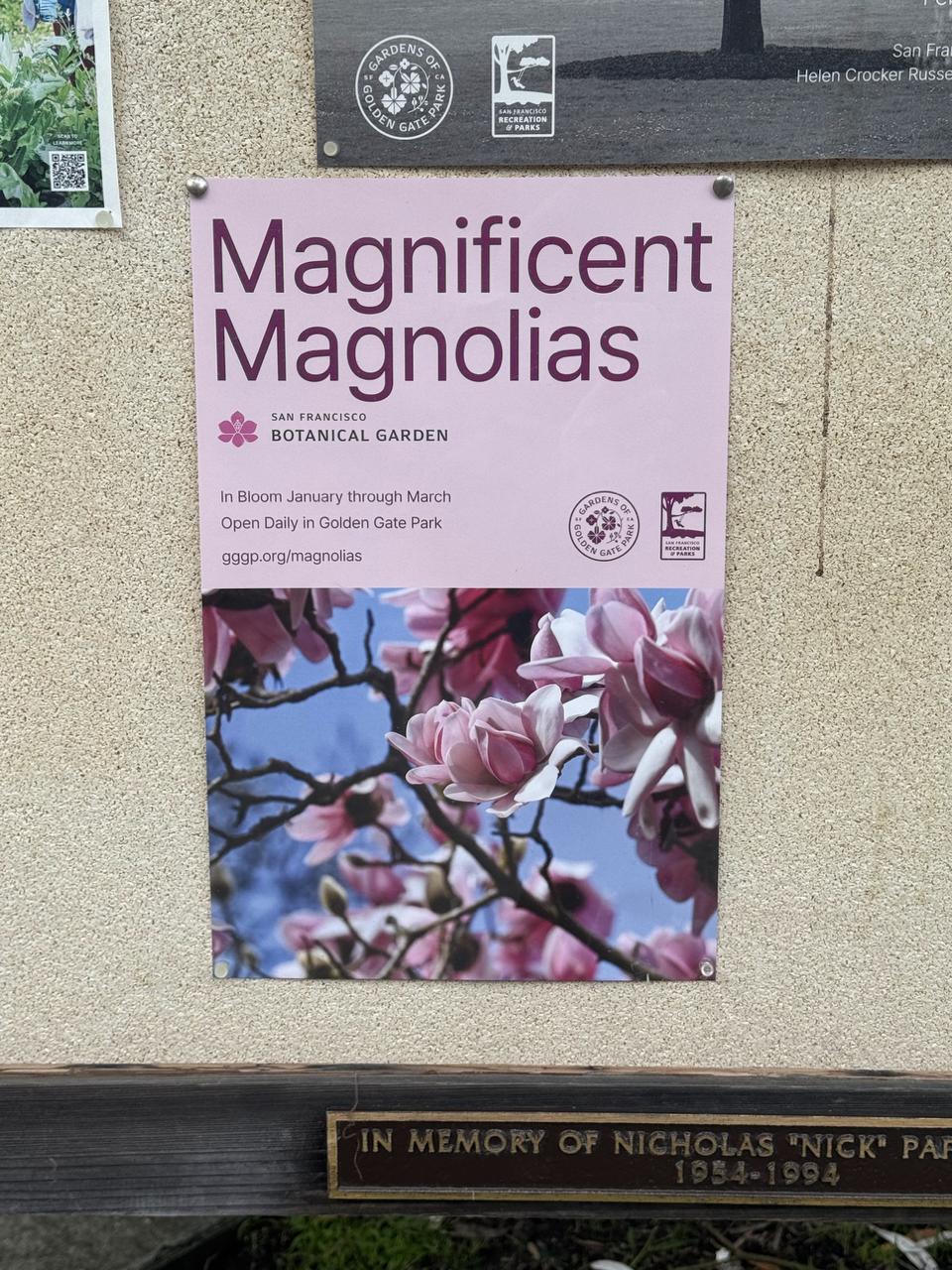
整个植物园里分布了各种不同的Magnolia flower,有的极大,有红的也有白的。也许是我没见过长高的玉兰树是什么样,我印象中玉兰树总是中等高度,花大叶大。也许植物园里的玉兰品种不同,形状也不同,且大玉兰树的枝桠会出现一种神奇的几何图形,非常规则,抬头看上去,背景是碧蓝的天空,仿佛被玉兰树的树枝切割成了一片,像是破碎的玻璃。

银杏
银杏是很亚洲的植物,但其实现在在美国也不少。在旧金山就有许多,最近我在唐人街图书馆旁边就发现一些,附近是一片小竹林。我前段时间在纽约野口勇博物馆门口也发现好几株,而博物馆内部还有一个日本园林,里面有红枫及松竹梅。说来奇怪,对于我来说,银杏如果和其他的亚洲植物种在一起,就特别显眼,但如果单单住在美国的街道上,就不太引我注意。

唯一我求而不得的植物是柳树,恐怕在美国是不可能找到「柳浪闻莺」的地方。如果有人见到杨柳,请告诉我。
落地生根
在日常生活里,因为旧金山本来就是一个亚裔偏多的城市,会有更多亚洲的植被,我是幸运的。我也一直好奇,对于别的文化的移民,它们是不是在马路上会看到一些被我无视的普通植物而被勾起乡愁。在美国的苏州园林日本园林仿佛是一个小小的盆景,浓缩式地提供了东亚人熟悉的元素,不知道其他人去哪里寻求他们自己的景致?
旧金山图书馆唐人街分馆里面写着「落地生根」四个大字,是为了和华人「落叶归根」抗衡。对移民来说,「生根」和「归根」是永恒的问题,结果最后都还是像无根之木到处漂流,回不去也留不下。你看,说了半天花木,其实在想的是故园。中国人的语境里,花木永远不止是花木,事情也被弄复杂了。
「他乡遇故知」的激动褪去之后,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植物也许不会是故乡的那些植物。在美国房子里种出来的桂花永远不会是那一株在我初中教室外面让我上课时沉醉的桂花,种出来的枇杷永远不可能是和妈妈一起散步时遇到然后一起采下来吃的的那一株,银杏也永远不可能是小学操场上那一棵。
